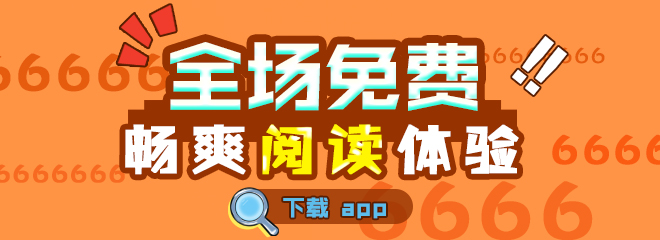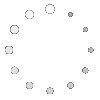8蒙古帝国政府组织与军队秩序的萌芽(1/5)
虽然除掉了萨满阔阔出,但新兴的蒙古帝国仍然保留了萨满教的宗教基础: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多少夹杂有祆教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分。大汗是神的体现,神仍然是腾格里,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上天,或波斯人所说的阿马兹达神那样的天神。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汉化的,还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化的,都称自己是腾格里(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的统治代表着腾格里的统治,反对他们就是与腾格里作对。
不儿罕·合勒敦山(今天的肯特山)高**立在斡难河河源处,成吉思汗本人似乎特别崇拜这座山上的神灵。在他发迹之初,蔑儿乞惕人曾把他的妻子掳走,他借助于飞奔的骏马,才得以逃脱,那时候他就是躲到这座山上避难的。他像一个朝圣者,立刻爬上了山,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摘下帽子,解下腰带搭在肩上,表示恭顺,然后跪拜九次,并用马奶酒(牧民们用马奶发酵制成的酒)奠祭。后来,在对金朝发动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前,他再一次来到不儿罕·合勒敦山,以同样虔诚的态度重复朝圣的行为,他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祈祷说:“永恒的腾格里!我已经武装起来,金人曾让我的祖先们羞耻地死去,我要为他们所流的血报仇。如果你允许我复仇,请助我一臂之力!”拉施特记下了这些话。据其他史籍记载,在出征前夕,成吉思汗将自己关在汗帐里,与神独处了三天。他身边的人不断地恳求上苍:“腾格里!腾格里!”第四天,这位得到天助的大汗终于走出了汗帐,告诉众人,腾格里将保佑他赢得胜利。
这种古代的宗教认为万物有灵,崇拜山峰和河源,从中发展出的仪式被***作家们和***传教士们记录了下来:登上圣山的顶峰,是为了离腾格里更近,便于呼唤腾格里;摘下帽子,把腰带放在肩上,表示恭顺,这是落在大汗本人身上的责任;如果打雷,那就暗示着行动要注意,也就是说腾格里生气了;禁止弄脏泉水,不准在小溪里洗澡,也不准洗衣服,因为那里是精灵栖息的地方(这个规定一开始还曾引起过穆斯
林社会的严重误解,因为他们特别讲究沐浴)。蒙古人敬畏上天,迷信巫术,同时也感觉到,明智的做法是不仅要信奉萨满教,还要接受其他的神明代表。换句话说,就是接纳任何可能拥有超自然力量的教派的首领们。比如,他们在克烈部和汪古部中发现了景教的牧师,在回鹘人与契丹人中还有佛教的僧侣,以及来自中国汉地的道士、西藏的喇嘛、方济各会会士或***的毛拉。蒙古人对各教派首领的包容,同时也为他们的腾格里信仰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障。因为广泛存在的迷信而变得格外包容,直到扎根于突厥斯坦与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不再像从前一样迷信敬畏,他们的世界观与行为才失去了宽容。
构筑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蒙古国家又从回鹘人那里借来了文明的工具,即文字与官方语言。前面提到过,1204年,乃蛮汗
(本章未完,请翻页)
8蒙古帝国政府组织与军队秩序的萌芽(2/5)
国被推翻时,成吉思汗起用了曾效命于塔阳汗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负责教导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教他们用回鹘字书写蒙古文,签署官方法令,并加盖塔马合(或称帝国的印玺)。在这些新生的事物中,可以看出中书省的萌芽。从1206年起,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为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是塔塔儿人,自幼就被成吉思汗和他的夫人孛儿帖收留与抚养。失吉·忽秃忽负责用回鹘字写蒙古文,记录审判的决议和判决,掌管表明蒙古各贵族所分到的百姓情况的花名册(被称为“青册”)。这些关于法律方面的初期工作为实用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家系手册,也就是伯希和所说的“一种蒙古的多齐埃(d’Hozier)”。①
成吉思汗的后裔们制定的“札撒”(yasaq),从字面上来看,意思是“规章”或者一般法典。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确定了札撒的蓝本(或者说是帝国**)。得到“天助”的大汗,通过札撒对他的人民和军队实施了上天规定的严格纪律(人民和军队几乎不分)。这部法典实际上相当严厉,凡是犯了谋杀、盗窃、密谋、**、以妖术迷惑人、接受贿赂等罪行的人,都必须处死。不管是军人,还是普通百姓,只要违反了法令,遵循一般法典,一律按犯罪论处。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即它是管理社会的有效纪律。成吉思汗的“名言”或“箴言”(bilik必里克)形成了这部法典的法理学范畴。遗憾的是,这些箴言与札撒一样都没能流传下来。
蒙古纪律带来的效果令西方探索者感到吃惊。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过了大约40年,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从蒙古回来后写道:“对于统治者,鞑靼人(即蒙古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服从性都要高得多,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神父对修道院院长的顺从。他们非常尊敬长官,从不对他们撒谎。除了小偷小摸的行为,他们之间很少争吵或发生谋杀。如果有人不小心丢了牲畜,捡到的人很有可能会物归原主,而绝不会据为己有。他们的妻子非常守节,即便尽情欢乐的时候也从不越礼。”如果有人将这幅图景与成吉思汗征战前夕蒙古境内的乱象进行比较,或者与今天蒙古人的道德水平进行比较,就会不由得惊叹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给蒙古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处于社会阶层最高一级的是成吉思汗的家族,即黄金家族(altan uruk),地位最高的是大汗,其次是大汗的儿子们,也就是王子(k?begün)。黄金家族在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域内行使财产权,采用的方式与大汗的祖先们在他们的草原故乡所实行的统治方式极其相似,尽管先祖们的领地要小得多。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都得到了各自的封地,划分给他们的草原领地后来形成了成吉思汗一脉的各个蒙古汗国。蒙古社会(或者也可以说是突厥-蒙古社会,因为成吉思汗在阿尔泰地区吸收了大批
(本章未完,请翻页)
8蒙古帝国政府组织与军队秩序的萌芽(3/5)
突厥部落)的政权仍然掌握在贵族手里。蒙古社会的阶层,包括完全自由(那可儿)的战士(或称亲兵)、普通百姓(也就是平民),以及通常是非蒙古人组成的奴隶(乌拉干,孛斡勒),他们都在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研究的古代“草原贵族”的统治和操控之下。“草原贵族”主要由勇士贵族(把阿秃儿)和部落首领贵族(那颜)组成。在这里,符拉基米尔佐夫对出身不同的阶层却以对个人的忠诚为纽带世代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社会的所有要素进行了区分。
在军队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封建等级。效忠于某个人,这一纽带将十夫长(阿儿班)、百夫长(札温)、千夫长(敏罕)和万夫长(土绵)联系在一起。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通常由地位较高的那颜担任。在他们以下,军队的骨干往往是自由人中的小贵族,他们被称作“达干”(蒙古语里称为“答儿罕”),这一称号来自古突厥。原则上,他们有权将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以及大规模狩猎中获取的猎物据为己有。顺便说一句,有些答儿罕因为勇猛过人而被提升为那颜。
符拉基米尔佐夫曾讲过,大汗的禁卫军是军队这一“贵族式的组织”里的精锐。禁卫军(K?shik怯薛,或译作“宿卫”)约由一万人组成,原则上分为值日班的士兵(土儿合兀惕)和值夜班的士兵,此外还配备有弓箭手豁儿赤(或称“箭筒士”)。“值夜班的人数是800至1000人,弓箭手是400至1000人。值日班的人数是1000人。禁卫军的实际人数最后达到了一万人。”只有贵族和来自有特权的自由人集团的答儿罕才有资格加入禁卫军。禁卫军中一个普通的士兵,他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其他军队的千夫长。成吉思汗的大多数将领都是从这支禁卫军中挑选的。
原则上,蒙古军队分为三翼,向南展开(蒙古人习惯的方向)。左翼军驻扎在东部,最初由札剌儿部的木华黎统率。中军由八邻部的那牙阿指挥,以及察罕(一位党项族青年,从小被成吉思汗收养,大汗对他像儿子一样)统领的千名精英禁卫军的。右翼军的统帅是阿鲁剌惕部人博尔术。成吉思汗去世的时候,蒙古军队的实际人数已经达到了129000人。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左翼军有62000人,右翼军有38000人,其余人则被分配到了中军和后备军中。
蒙古军南向的队列与它的出击目标是相符的,它以南方各国为出击目标,呈扇形展开。左边的目标是中原;中间的目标是突厥斯坦和东伊朗;右边针对的是俄罗斯草原。
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这位蒙古勇士究竟长什么样子?以赵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画家们将他的画像惟妙惟肖地画了出来。游历了蒙古之后的史学家费尔南德·格瑞纳德在成吉思汗的传记里所作的描述,给读者的印象就像是看到了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绘画大师的画卷。他写道:“这位住在帐篷里的战士,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穿着长筒毡袜和皮靴子,外罩一件长至膝盖以下的皮衣。在战场上,他戴着皮制的能把
(本章未完,请翻页)
8蒙古帝国政府组织与军队秩序的萌芽(4/5)
后颈遮住的头盔,穿着用黑色皮条编织而成的、坚固而又柔软的胸甲。他的进攻武器是两张弓弩和两个装满箭支的箭囊、一把弯弯的马刀、一把短柄手斧、一把悬挂在马鞍上的铁钉头锤和一支能把敌人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长矛,还有一条有活结的马缰。”
蒙古人与他们的战马形影不离。事实上,他们与战马之间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出生在同一片草原,在同样的土地上成长,经受了同样气候的考验,接受的锻炼也是一样的。蒙古人身材矮小结实,骨骼大,体格强健,有着超凡的忍耐力。蒙古马虽然体态并不优美,但矮小而壮实,它们有着“强有力的脖子和粗壮的腿,身披厚厚的毛,蒙古马烈性十足,精力充沛,耐力超强,步履平稳,令人称奇”。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掌握了驯马技术的印欧人正是因为北方游牧民的这种战马而占据了优势;在上古时代末期,匈奴人骑着它征服了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到了中世纪,新的活力将把草原上的所有骑手推向燕京、桃里寺(今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和基辅的金色宫殿。
关于蒙古人的战术,已经有很多记载。有些人把它与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的战术进行对比。在一些高级军事会议中,蒙古人拟定的战术被卡洪看作是天才的妙想。从本质上来讲,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所使用的古老战术的完美形式,这种经久不衰的游牧战术是从不断袭扰耕地边缘和在草原上举行的大规模狩猎的实战中总结发展而来的。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里,记录了他的名言:“白天要像老狼一样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晚上要像乌鸦一样瞪大眼睛留意四周。作战的时候要像猎鹰一样勇猛地扑向敌人。”在围猎鹿群的过程中,耐心地潜近猎物,这样的狩猎经验使牧民们学会了暗地里派出许多隐蔽的侦察人员去观察猎物或打探敌人的动静。在狩猎的过程中,常使用拍打器,他们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了战争中,展开了拦截行动。在拦截行动中,牧民们会从两翼包抄敌军,就像他们在大草原上拦截逃跑的野兽一样。
靠着这支行动高度机动灵活的骑兵,游牧民族常给对手造成从天而降的感觉,带来草木皆兵的效果,导致对手还没有与他们交锋就已经仓皇失措了。如果对手坚守阵地,蒙古军队并不会坚持强攻,而是采取所有草原劫掠者惯用的方式,分散,隐藏。一旦拿着长矛的中原军人、花剌子模人、阿拉伯的马穆鲁克或者是匈牙利的骑兵们放松警惕时,他们又会伺机而动,卷土重来。在这些蒙古骑兵假装后退的时候,如果对手尾随追击,那么这些犯了错误的追随者可就倒霉了,他们会被带入迷途,远离自己的阵地,进入蒙古骑兵的伏击圈里,像被围猎的公牛一样地被砍死。在主力部队之前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主要负责射箭,万箭齐发的流矢将在敌人的阵营中开辟出一些致命的空隙。蒙古人与古代的匈奴人一样,也是骑射手,他们自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射箭术精湛,百发百中,一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
(本章未完,请翻页)
8蒙古帝国政府组织与军队秩序的萌芽(5/5)
码开外的人。骑术与射箭术精湛,再加上灵活机动而难以捉摸的作战习性,蒙古骑兵有着难以匹敌的作战优势。对于自身的优势,蒙古骑兵相当自信,前锋部队的射箭是轮换的,放完一排箭就换后面的替补,如此循环。直到敌人已经被引出阵地,或者是被这种远距离的射击打乱了阵脚时,居中的重骑兵才会出击,他们用长刀将敌人砍倒。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蒙古人还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体格、丑陋的外貌和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给敌人造成心理上的震慑。他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地平线上,迅速散开;在可怕的静谧中,听不到任何口令指挥,他们只看旗手的手势,悄无声息地前行。然后,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嘶吼着发起突然冲锋。
这种传统计策由来已久,当猎人们捕猎时,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使猎物发狂、迷茫,然后将它们抓住。骑在战马上的蒙古人,像捕猎羚羊或老虎一样地劫掠中原人、波斯人、罗斯人和匈牙利人。蒙古的弓箭手像射下展翅高飞的鹰一样,击倒精疲力竭的骑士。蒙古人的战术运用得最精彩的时候,是在对河中和匈牙利发起的战争中。这些战争都具有大规模围猎的性质,在以系统的屠杀结束对“猎物”的追逐之前,蒙古人设计了使“猎物”疲累、恐惧、耗尽精力和包围他们的方法。
普兰诺·卡尔平尼的观察极其敏锐,他对蒙古人的战术进行了生动描述:“一旦他们发现敌人,就会立刻展开进攻,每个人都向敌人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发现无法打败敌人,就会马上撤退,回到自己的阵营。这样做,其实是一种诱敌深入的伎俩,一旦敌人追赶,就会被诱骗进入他们事先埋伏好的地方。如果他们发现敌人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就会立刻骑马离开,停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沿途一路攻击并抢劫……他们也可能在精心挑选的地方扎营,一旦敌军经过,他们就会展开突袭……总之,他们的战术层出不穷。蒙古人还会派出一支由俘虏和随同他们出征的其他族人组成的辅军正面迎敌,而他们的主力则从左、右两翼包抄敌人。这种战术非常有效,能使敌人误认为他们人数众多。如果敌人顽强抵抗,蒙古军队就会故意让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在敌人四散逃窜时,蒙古军队就会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在1241年的绍约河战役中,速不台就使用了这一战术)。不过,他们会尽量避免与敌人进行肉搏战,而尽可能地用箭射伤或射死敌方的人马。” 蒙古人在大规模的狩猎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这一场景出现在卢布鲁克的描述中:“当他们打算狩猎时,就会大量聚集在野兽出没的地方,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像一张网一样罩住猎物,直到最后用箭把它们射死。”
①类似于多齐埃17世纪的著作《法国主流家庭族谱》(〈Généalogie des principa*** f***l*** de France〉)。伯希和在《(突厥斯坦)评注》38页和40页以下,纠正了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