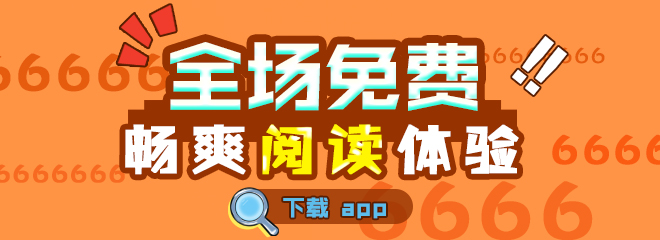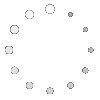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1/5)
从公元前35年起,当年西迁的匈奴就消失了踪迹。不肯归附汉朝的郅支单于带着一些匈奴部落迁移到了咸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的草原,不久就被一支远征的汉军(副校尉陈汤所率领的汉军)打败,郅支被杀死。他带到那一地区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那里停留了几个世纪。然而,由于他们周围缺乏有文化的邻邦,因此没人记录下他们的活动和冒险,以致我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历史。直到公元4世纪,当他们进入欧洲,与古罗马世界产生联系时,我们才再一次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
自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提亚人取代了斯基泰人开始,这些与斯基泰人一样属于北伊朗人种的萨尔马提亚人,就一直占据着黑海北岸的俄罗斯草原。他们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活动范围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德涅斯特河之间。后来,包括阿兰人(《史记》中称他们为“奄蔡人”)、罗科索拉尼人以及雅齐基人在内的几个萨尔马提亚部落逐渐过上了一种独立的生活。其中,阿兰人在捷列克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延伸到了库班;而罗科索拉尼人自公元62年以后就一直居住在顿河下游西岸;至于雅齐基人,他们从公元50年起就占据着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平原地带,这片平原位于达西亚(古罗马尼亚的国家)与罗马帝国潘诺尼亚行省之间,也就是今天的匈牙利中部地区。萨尔马提亚人与罗马帝国被巴斯塔奈(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分隔开来,这种情形直到公元106年图
拉真吞并了达西亚之后依然没有改变。巴斯塔奈人是自公元200年起就从喀尔巴阡山北面的道路沿着德涅斯特河顺流而下,一直到达河口的东日耳曼人,这次迁徙是已知的日耳曼人的第一次“东进”(即向东方扩张)。公元200年前后,一支新的日耳曼势力(源自瑞典的哥特人)从维斯瓦河下游入侵,这对萨尔马提亚人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控制权造成了威胁。公元230年,哥特人的迁徙中止,他们开始攻打位于黑海岸的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当时,在俄罗斯南部地区,以第聂伯河为分界线,哥特人占据着下游西岸一带,而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以及其他各部落)则控制着东岸一带。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仍然是希腊罗马式的附属国,臣属于恺撒及其他罗马皇帝。哥特人内部也分裂成了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控制着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的地区,西哥特人掌握着德涅斯特河下游到多瑙河之间的地区。罗马皇帝奥里利安于公元270年撤出达西亚,于是,第三支哥特部落,也就是格庇德人马上占据了达西亚。这一时期,正是发现于基辅南部的切尔尼亚霍夫的哥特式古墓修建的年代,也是位于第聂伯河下游赫尔松城附近的尼古拉耶夫卡古墓所处的时代(公元3世纪)。在萨尔马提亚人方面,这一时期也是由库班地区的第比利斯卡亚、沃兹德维任斯科耶、阿尔马维尔和雅罗
斯拉夫斯卡亚所组成的古墓群的年代,墓群中发现了具有萨尔马提亚艺术特征的饰牌和扣环。同一时期,芬兰-乌戈尔各民族无疑遍布
(本章未完,请翻页)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2/5)
于北方的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大森林。在喀山附近,萨尔马提亚人对皮亚诺波尔文化(约公元100年-公元300年或400年)有着显著的影响,皮亚诺波尔文化是安纳尼诺文化地方化之后的一种形式。由此往西,在卡卢加文化群里发现了一些扣饰,它们带有公元3世纪-公元4世纪日耳曼-罗马艺术的特征。以上就是在匈奴人到来之前,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各民族及文化的基本发展情况。
至于这些有着重要历史影响的匈人(西匈奴的后裔),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咸海以北的草原而进入欧洲,我们尚不得而知。公元374年前后,这些匈人从伏尔加河下游渡河之后,在被约尔达尼斯①叫作巴拉米尔或巴拉姆贝尔的首领的率领下,继续高歌挺进,跨过顿河,打败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并迫使他们臣服;接着又攻击了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年迈的东哥特国王厄尔曼奈瑞克战败,万念俱灰之下自杀。他的继承人维席密尔也战败,被匈人杀死。至此,匈人统治了大多数的东哥特人,而西哥特人则于公元376年渡过多瑙河,逃到罗马帝国,避开了匈人的攻击。最先被打败的阿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继续留在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旧地,被迫暂时屈从于匈人的统治。公元10世纪前后,那些留下来的阿兰人在当地皈依了东正教,他们的后裔就是今天的奥塞梯人。而另一些不愿臣服于匈人的阿兰人则开始向西迁徙,参与了西日耳曼人的大入侵。这些西迁的阿兰人中,有一些部落后来定居在了卢瓦尔河下游的高卢;而另一些则进入了西班牙,与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维人结合,或者与西哥特人结合,形成了混种人,于是混合之后的人种得名加泰罗尼亚(即哥特-阿兰人)也就不难想象了。
关于匈人入侵古罗马和日耳曼人的世界的恐怖情形,在阿密阿那斯·马塞林(罗马史学家)和约尔达尼斯的著作里有充分表述。马塞林写道,“匈人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凶猛和野蛮。他们划破自己孩子的面颊防止以后长出胡子。他们有着畸形的外表,身材粗壮,手臂奇长,头大得与身体不成比例。他们过着野兽一样的生活,吃生的东西,比如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还不放任何佐料。他们完
全不知道使用犁来耕作,也不知道可以居住在房子或棚子等固定的住所里。长期的游牧生活,使他们从小练就了对寒冷、饥饿和干渴的耐受力。他们带着牧群和妻儿四处迁徙,妻儿住在牲畜拉的篷车里。女人们在车里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长大。如果有人问他们从哪里来,出生在哪里,他们根本回答不上来。他们的衣服充其量不过是一件深色的粗麻布袍和一件用鼠皮缝成的外套,麻布袍子穿上身后再也不换,直到穿坏为止。他们一身的戎装,就是反戴头盔或帽子,毛茸茸的腿上裹着羊皮。他们的鞋子,既没有样式,也没有尺码的区别,这导致他们根本不适合长时间步行,所以他们无法组成步兵作战,但他们很擅长骑马,几乎像钉在了他们丑陋而矮小的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
(本章未完,请翻页)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3/5)
疲累,奔跑起来快得就像一道闪电。他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女人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打仗的时候,他们发出可怕的嘶吼,冲向敌人。一旦受到阻挡,立即分散,马上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阻挡他们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的观念里,根本没有建造防御工事或是加固营防这类概念。但他们有着无可匹敌的射箭技术,他们能在难以想象的距离之外射出
箭矢,箭头像锋利的骨头一样坚硬,像铁一样具有杀伤力”。
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里斯(高卢诗人)认为,匈人的畸形体形是从孩提时代就慢慢形成的。提到这些短头颅的人们,他的口吻透露着厌恶,他说他们鼻子扁平(“一个扁平无形的肉瘤”),颧骨突出,眼睛深陷在黑洞洞的眼眶里(“然而他们锐利的目光却时刻留意着远方”)。游牧民习惯于用鹰一样锐利的目光观察着广阔的草原上的一切动静,他们能够分辨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的是鹿群还是野马群。这位作者还用优美的诗歌来描述这些草原上永远的骑士:“站在地面上,他们是矮人;跨上骏马,匈人是世上最伟岸的人。”
把这些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对匈奴人的描述进行一下外貌上的对比,会发现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在体型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匈奴人与这些匈人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跟中国古代和信奉***的其他国家所流传下来的13世纪的蒙古人的肖像特征也是一样的。无论是短头颅、头大、身壮、腿短的匈人和***,还是蒙古人,都是常年驰骋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是来自亚洲高原上的骑射手,他们游荡在耕地的边缘,在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过着定居生活的文明社会的袭扰。
阿兰人与东哥特人臣服于匈人,西哥特人逃离,于是从乌拉尔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阔草原全都成了匈人的囊中之物。接着这些匈人又从喀尔巴阡山山道通过,或经由瓦拉几亚平原,侵占了匈牙利平原,迫使当地的格庇德人臣服,他们于公元405年-公元406年继续从匈牙利平原向外扩张,到达了多瑙河右岸。这个时候,匈人内部似乎已经分裂成了三支独立部落,公元425年前后,鲁阿斯(Ruas,“Rugas卢噶斯”或“Rugila卢吉拉”)、蒙杜克(Mundzuk,或“Mundiukh蒙迪乌克”)和奥克塔尔兄弟三人同时掌权,各领一支匈人部落。公元434年,这些部落全都被蒙杜克的两个儿子布莱达和阿提拉所掌控,不久阿提
拉就除掉了布莱达。
从此,阿提拉开始了他的称霸之路。公元441年,阿提拉向东罗马宣战。他跨过多瑙河,沿着今塞尔维亚境内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一路攻占纳伊苏斯(即今天塞尔维亚的尼什),劫掠菲利普波利斯(今天保加利亚南部的城市普罗夫迪夫),践踏色雷斯,洗劫了阿卡迪奥波利斯(即今天土耳其的“吕莱布尔加兹”)。公元448年,东罗马帝国与阿提拉和谈,被迫将多
(本章未完,请翻页)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4/5)
瑙河以南的大片领地割让给他,这片地区南北跨度从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到斯维什托夫,东西则自多瑙
河一直延伸到尼什。
公元451年1月至2月,阿提拉在匈牙利草原集合自己的部队之后,进军高卢,聚集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也加入了他征战高卢的队伍。他的部队在渡过莱茵河后,开始攻击当时仍由罗马贵族埃提乌斯统治的部分高卢地区。4月7日,阿提拉在梅斯城里纵火,接着又围攻奥尔良。7月14日,埃提乌斯掌握的罗马军队和隶属于狄奥多里克国王的西哥特军队前来援救,解除了奥尔良之围。阿提拉率部往特鲁瓦方向撤退。公元451年6月底,驻扎在特鲁瓦以西莫里亚库斯的阿提拉,与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展开了一场激战,他继续前进的步伐被阻止住了,尽管这一仗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它至少暂时使西方世界免遭侵占。
这一仗结束后,阿提拉退回到了多瑙河畔,整个冬天都待在那里。公元452年春,阿提拉重整旗鼓,展开了对意大利的进攻,但是阿奎莱亚城久攻不下,拖住了他前进的步伐,在耗费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最终攻陷了这座城,并摧毁了它。接下来他攻占了米兰和帕维亚,叫嚣着要攻占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闻风而逃。不过,阿提拉并没有挺进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心罗马,而是接受了罗马主教圣利奥一世的劝阻(公元452年7月6日),利奥一世承诺交纳贡赋,并把罗马公主霍诺丽亚嫁给他。于是阿提拉再次退回潘诺尼亚,最终于公元453年在那里去世。
记载了哥特人历史的约尔达尼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阿提拉画像,这幅画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中的阿提拉有着典型的匈人相貌:矮个子、宽胸膛、大脑袋、深陷的小眼睛、塌鼻梁。皮肤黑得像炭,留着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阿提拉发火的样子让人感到恐惧,而制造这种恐惧正是他用来震慑政治对手的一种武器。从他身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所描述的六朝时期入侵的匈奴人的自私和狡猾。他说话的时候常常故意加强语气,或者话语里隐含着威胁,这是他战略的第一步;而他进行系统性的破坏(比如阿奎莱亚城被阿提拉的铁蹄夷为平地,这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和***的初衷其实是想要给他的对手们一个教训。在约尔达尼斯和普里斯卡斯的描述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被自己的臣民看作是公正而廉洁的法官,对下人非常慷慨,对那些真正归顺于他的人也很和气。尽管他的那些蛮族同伴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却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当其他人用着金子做的餐具时,他用的仍然是木质的浅盘子。在同一份史料里,他除了具备这些特质,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他很迷信,盲目轻信身边的巫师;酷爱烈酒,每逢庆典必定酩酊大醉。不过,他时刻非常防备着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和书吏们,比如奥格瑟斯这样的希腊人,以及奥里斯特斯这样的罗马人,还有埃德科这样的日耳曼人。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游牧部落领袖的典型特征是他有
(本章未完,请翻页)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5/5)
着灵活而多变的政治手腕儿,
而不是动不动就与人厮杀。即便参战,他的表现也让人感觉到他首先是一位指挥官,而不是一员冲杀战场的猛将。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尊重法律,因此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外交借口。他所拥有的这些品质加上他照章办事的行为,使得他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能使正义站在他那一边。这些品质使人不由得想起草原帝国的另一位缔造者,又一个草原骄子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缔造的虽然是蒙古人的帝国,但他的麾下不仅聚集着蒙古游牧民,还网罗了不少来自亚洲高原的***和通古斯人;阿提拉帝国的构成也像成吉思汗的帝国一样,虽然主体是匈奴人(可能是***),但同时也吸纳了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东哥特人、格庇德人以及分布在乌拉尔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其他异族人。帝国衰亡的隐患就埋藏在这里。公元453年,阿提拉去世,他一手创建的凝聚了各个民族的帝国也随之迅速土崩瓦解。首先起来反叛的是东哥特人和格庇德人,他们与匈人在潘诺尼亚进行了一场大战,匈人战败,阿提拉的长子艾拉克被杀(公元454年)。
后来,阿提拉的另一个儿子邓吉西克(也可能名叫“丁兹吉克”)带着匈人往俄罗斯南部地区撤退。阿提拉其他的几个儿子厄尔纳克、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则找罗马人要土地,罗马人把多布罗加(或“杜布鲁亚”)给了厄尔纳克,其他的两位则被安置在了梅西亚。邓吉西克率领匈人在多瑙河下游附近发起了对东罗马帝国的进攻,不料兵败被杀。阿提拉之子邓吉西克被砍了头。公元468年,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他的头被拿出来示众。
那些在黑海北岸幸存下来的其他匈人氏族,分成了两支部落,即游牧于亚速海西北一带的库特利格尔部,以及游牧在顿河河口附近的乌特格尔部。两支部落不久就变成了敌对的双方,暗地里挑起他们之间的争端正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外交策略。公元545年前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煽动乌特格尔部的首领桑蒂尔克攻击他的对手库特利格尔部。公元548年,大批库特利格尔人遭到桑蒂尔克屠杀。但不久,库特利格尔人在他们的首领扎伯尔干的带领下,奋起反击,对支持他们敌人的拜占庭进行报复。公元558年冬天,趁着多瑙河结冰,扎伯尔干率部越过河面,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下,但是贝利萨留(拜占庭帝国一代名将)挽救了这座都城的危亡。扎伯尔干退回顿河草原,继而展开了讨伐桑蒂尔克的军事行动。这两个部落从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厮杀,直到第三者阿瓦尔人的出现。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打败了库特利格尔部和乌特格尔部,并占据了俄罗斯草原,才最终结束了这两部之间的自相残杀。这个新的外来势力的入侵,是由突厥(或历史上的***)在亚洲大陆所引起的一系列局势的改变而带来的连锁反应。
①约尔达尼斯是拜占庭的作家,代表作有《哥特史》,这本著作写于公元6世纪中期东罗马帝国与哥特人发生战争期间。
突厥、回鹘和契丹中世纪初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