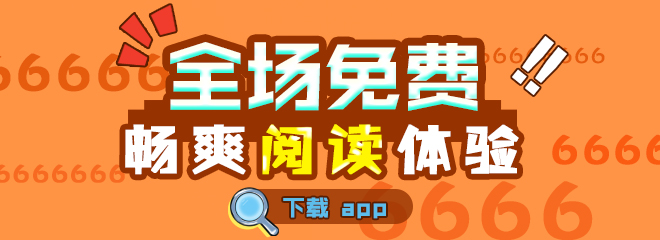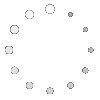14东汉时期塔里木绿洲的文明(1/5)
东汉时期,汉王朝控制着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个绿洲地带,确保了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频繁顺畅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贸易与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印度佛教徒们正是通过这条路来到喀什噶尔和中原传教),把希腊-罗马艺术带到了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梅斯·蒂蒂亚诺斯委派到中国的人与佛教传播者们的活动有着同样的目标。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丝绸之路南线,也就是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线。奥瑞尔·斯坦因带领的探险队,在古于阗(约特干)发现了罗马皇帝瓦伦斯统治时期(公元3**年-公元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拉瓦克,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组有着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浅浮雕,佛像身上的希腊服饰雕工非常细腻。稍微偏东方向,在尼雅,探险队找到了一个存在于公元3世纪末期,早已废弃的古城遗址,遗址里出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原鄯善国境内的米兰,他们发现了一些精美的希腊式佛教壁画,画面上的形象主要是佛陀和僧侣以及天使。这些长着翅膀的天使,外貌带有明显的罗马-亚洲特点。这些壁画上都标注着印度字“Tita”(经研究鉴定,已经确认“Tita”一名就是“Titus”),很明显,这些壁画的年代都在公元3世纪-公元4世纪之间。
当汉代国内处于局势稳定时,大批佛教传播者相继穿过这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帕提亚人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抵达中国,一直待到了公元170年在中国去世。公元170年前后,印度人竺佛朔和月氏人(也就是印度-斯基泰人)支谶都来到了中国,他们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公元223年至公元253年,一位月氏使者的儿子名叫支曜的,把一些佛经翻译成了汉文。说起这些月氏人,他们非常有意思,正是这些来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的使者们,通
(本章未完,请翻页)
14东汉时期塔里木绿洲的文明(2/5)
过丝绸之路,将佛教带到了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地区,这也就意味着丝绸之路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作用。除了这些来自贵霜帝国(或印度)的传教者之外,还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帕提亚人继续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进行着改宗的工作,了解这些仍然是有价值的。在中国的大藏经中,记录着那些经由塔里木盆地进入中原传教的佛教使者和译经者的名字。在塔里木地区,一群来自伊朗东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僧人从事着译经工作,他们将神圣的梵文手写本翻译成东伊朗语、龟兹语等各种方言。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很有必要回顾一下,那就是声名远播的鸠摩罗什(公元344年-公元413年)的事迹。
鸠摩罗什祖籍印度,他出生于龟兹贵族家庭。鸠摩罗什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情愿放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寺院潜心礼佛,但是龟兹王强留他继续做官,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继而有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从小跟随在母亲身边,在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学。当他返回塔里木时,游历疏勒(喀什噶尔)并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疏勒与龟兹一样,都是印度思想的活跃中心,这两个城市的统治者争相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的宫里,并以此为荣。当鸠摩罗什回到龟兹时,龟兹王帛纯(汉译音)亲自迎接他,而莎车王的两个孙子则拜他为师。直到公元382年-公元383年汉人将领吕光(后凉政权的创立者)入侵龟兹,鸠摩罗什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祖籍克什米尔)一直都住在龟兹。攻占龟兹之后,吕光把鸠摩罗什带回了汉地。据说吕光见到龟兹的宫殿时,大吃一惊,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龟兹的宫殿是多么宏伟壮观。人们推测,吕光之所以感到惊讶,是因为在龟兹所看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都是传统的印度和伊朗式的,而不是采用的中国样式,也就是说,事实可能与哈钦的看法一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创作于这一时期前后。
就像
(本章未完,请翻页)
14东汉时期塔里木绿洲的文明(3/5)
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亚洲大陆的文明分布在两个明显的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再到鄂尔多斯,盛行着草原艺术。精心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显然是起装饰作用的程式化动物形象,是草原艺术的典型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绿洲上,生活在环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带上的居民中,流行着受到希腊艺术、伊朗艺术和印度艺术直接影响的绘画、雕塑艺术。希腊艺术、伊朗艺术和印度艺术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而且由于佛教的需要,它们的表现形式都带上了佛教色彩。
塔里木艺术起源于阿富汗地区,时间要追溯到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公元4世纪,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贵霜王朝晚期的几位皇帝深受波斯的萨珊王朝的影响,并被纳入了萨珊王朝的扩张范围,根据赫兹菲尔德和哈钦对贵霜-萨珊钱币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点。印度与伊朗边境的这些地区,诞生了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巴米扬石窟和卡克拉克石窟中创作于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的精妙绝伦的壁画,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这些壁画中所描绘的图案和服装,还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处理,都清晰地反映了萨珊文化的影响。在离喀布尔不远的凯尔卡纳,哈钦找到了一尊公元4世纪末的萨珊式婆罗门雕塑;在喀布尔-巴克特拉公路之间的鲁伊附近,即杜克塔-依-奴细尔汪,发现了纯萨珊式的壁画群,其中有一个画面最具代表性,
它表现的是公元5世纪萨珊王室的一位王子、巴克特里亚总督。这些发现都是哈钦-哥达德和哈钦-卡尔探险队找到的,它们有力佐证了上述观点。通过这些壁画,我们猜想,印度宗教、文学与萨珊王朝的沙普尔和科斯罗伊斯时代的波斯物质文明,在当时的阿富汗高度融合。
这就是萨珊文化与佛教结合的产物,被佛教传播者们,也就是继鸠摩罗什之后的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们,播撒在了塔里木各绿洲以及丝绸之路上的每一站。多
(本章未完,请翻页)
14东汉时期塔里木绿洲的文明(4/5)
亏了他们的活动,才使得宗教能够沿着丝绸之路传播。早期的克孜尔(库车稍微偏西)石窟壁画与巴米扬石窟壁画,在风格上有一定关联,具有造型极富立体感、线条柔和、用色考究的特点,多使用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浅绿色、深棕色等颜色。关于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年表的制定,应归功于哈钦,他把这种艺术风格出现的时间追溯到了公元450年至公元650年。在这种早期的壁画中,最具影响力的仍然是印度艺术风格,壁画中还有旃陀毗罗婆王后之舞,它使人联想到印度阿旃陀石窟中精美的**画像。萨珊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的壁画,画家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年轻的伊朗君主,他的着装模仿伊朗服饰,上穿有着库车式的大翻领(参见哥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扬壁画)、收腰的浅色紧身上衣,下穿裤子和高筒靴。1937年,哈钦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凡杜克斯坦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灰墁,根据其中一枚铸造于萨珊王库思老二世时期(公元590年-公元628年)的钱币可以确定它的年代,这些灰墁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斯文化与佛教融合,对阿富汗地区的影响,使那里直到被阿拉伯攻占之前仍然在模仿通用龟兹语地区的男性
服饰。
哈钦认为克孜尔壁画中期风格的时间为公元650至公元750年,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壁画造型不固定,色彩较为明快(多使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而人物服饰则主要表现出萨珊式的特点。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木吐拉佛教壁画中,刻画了男女信徒列队前行的场景,再现了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的龟兹宫廷。画面上那些穿着华贵服饰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服饰和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波斯文明的影响,就像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学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一样。除了这种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还选取了一些军事题材作为表现场景,比如“瓜分圣物”的场景,它反映了全副武装的龟兹武士的“骑士风姿”
(本章未完,请翻页)
14东汉时期塔里木绿洲的文明(5/5)
,武士们头戴锥形头盔,身披战甲,手持长矛,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古称“蓬吉卡裴”)一带的萨尔马提亚骑手。
在塔里木南部地区,也发现了波斯文明与佛教结合的产物,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块公元7世纪末的木板画,它出自于阗东北绿洲一带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在这幅画上,有着成队纯印度式的**龙女,她们的形象类似于阿旃陀石窟壁画中最优雅的**人像;具有波斯特征的牧马人和赶骆驼的人;还有一位留着胡须的菩萨,头戴古波斯式头巾,穿着绿色长上衣和裤子,脚上的靴子是萨珊贵族常穿的样式。最后,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也同样可以看到波斯文明的影响,典型的就有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壁画,以及穆尔吐克的壁画。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中,身披胸甲的神像使我们联想起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里一位穿着萨珊式铠甲的龟兹骑手,以及哈钦所记载的某座保留着纯粹的印度风格的观音像。在穆尔吐克的壁画中,菩萨有着印度式的外形,旁边是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中甲胄一样的胸甲的信徒,他们的头盔上装饰着张开的翅膀,显然这些都与萨珊波斯文明密切相关。这种结合在雕塑方面的体现,可以参见斯坦因爵士在焉耆所发现的泥塑像,它们精致而小巧,简直组成了一个展示民族文化的画廊。它们看起来极像阿富汗的哈达(Hadda)的希腊式佛像,这些佛像现藏于吉美博物馆。由此可见,直至公元8世纪下半叶,在突厥各部落征服塔里木南、北两缘的绿洲之前,从莎车到于
阗再到罗布泊,从疏勒、龟兹、焉耆到车师,这些地区的文化既不是来源于阿尔泰文明,也不是来源于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古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此外,古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能够传入中国内地,也要归功于这些绿洲。伯希和率领的探险队与斯坦因所率领的探险队,分别在敦煌(这里是丝绸之路在甘肃经过的第一站)附近发现了佛教壁画和画幡,这些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