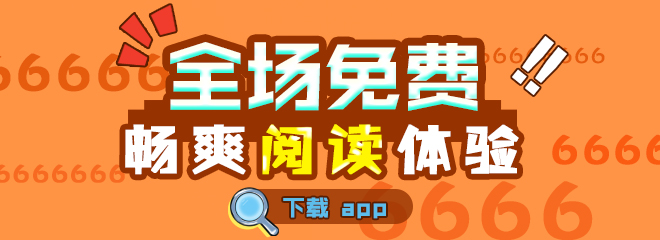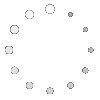6匈奴的起源(1/5)
当草原的西部地带,也就是俄罗斯南部地区被属于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占领时,他们无疑还控制着图尔盖河流域和西伯利亚西部地区;而草原的东部则处于突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在这些草原霸主之中,为古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被他们称作“匈奴”的民族。对于这一蛮族的称呼,“匈奴”这个名称的词源,与后来罗马人、印度人所称的“Huns(Hunni)”和“Huna”是一样的。或许,在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时,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匈奴”一名才开始明确出现在中国的编年史中)已经被中原人称为“玁狁”。在此之前,他们可能被称为“獯鬻”,或更笼统地被称作“胡人”。先秦时期,中原人所了解的胡人是指当时那些居住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以及河北北部等中原边境地区的民族。马伯乐猜想,盘踞在北京以西以及西北的“北方的戎族”也就是北戎(即“山戎”),是一支胡人部落。公元前4世纪,其他的北戎氏族都已经归顺于赵国。赵武灵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325
年-公元前298年)甚至从他们手里夺取了山西最北边的地区(大同一带),实际上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他还夺取了鄂尔多斯北部地区。为了有效抵御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确保本国安全,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都将他们笨重的车兵部队改为了灵活的骑兵队。这一军事改革也彻底颠覆了中原人的着装习惯,古代的长袍被替代,他们像游牧民族的骑兵那样穿着长裤。中原的武士们还借鉴游牧民的穿戴
(本章未完,请翻页)
6匈奴的起源(2/5)
,头戴有毛的帽子,上衣有“三条尾巴”,系着带扣,这类带扣后来对“战国时期”的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抵御匈奴的进犯,赵国以及与它相邻的一些国家都纷纷沿着北部边境修筑防御城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逐渐完成了防御墙的修筑,是为万里长城。
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在首领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似乎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单于的全称是撑犁孤涂单于①,翻译成汉语意思是“天子”。从这些词里可以找到突厥-蒙古语的词根,尤其是“撑犁”,它是突厥-蒙古语中“Tangri”一词,意思是“天”。单于的手下有两大显贵,左右屠耆王,意思是左右贤王②。汉语音译的“屠耆”与突厥语词中的“doghri”有关联,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游牧民族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根据他们所说的固定居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那里后来成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所在的地方。原则上来讲,左贤王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成为单于的继承人,他住在东边,可能在克鲁伦河流域上游一带。而右贤王的所在则可能与阿尔伯特·赫尔曼的想法一样,他住在西边的杭爱山区,乌里雅苏台附近。在两位贤王以下,匈奴的统治阶层根据官阶高低排列依次是: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再往下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中的每一员,在行进的过程中都像有组织的军队一样有序。突厥-蒙古人形成的各民族习惯于向南进发,匈
(本章未完,请翻页)
6匈奴的起源(3/5)
奴的后裔、6世纪的***以及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也有同样的趋向。
汉人描绘的匈奴人肖像所具有的特点,我们也同样可以在继承了匈奴人外形特征的***和蒙古人身上看到。“他们个子很矮,”维格(中文名戴遂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概括说,“体格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高颧骨,塌鼻子,嘴唇上的胡须很浓密,而下巴上只有一小撮硬胡茬,穿了孔的长耳垂上戴着一只耳环。头发几乎都剃光了,只在头顶保留着一束。浓眉杏眼,目光炯炯。他们穿着长及小腿的宽松长袍,长袍的两边开衩,用腰带束缚,腰带的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天气寒冷,袖口在手腕处收紧。他们肩上披着一条皮毛做的短披肩,头戴御寒皮帽。他们的鞋子是皮做的,用一条皮带将宽大的裤子在脚踝处捆扎紧。垂在左腿前面的弓箭袋系在腰
带上。箭筒也挂在腰带上,贴近背部,箭头朝向右边。”
无论是匈奴人还是斯基泰人,他们的衣服细节是相同的,尤其是裤腿靠近脚踝的地方收紧。他们的很多习俗也是相同的,比如殉葬。在部落首领的墓葬里,匈奴人和斯基泰人都会杀死首领的众位夫人以及仆人们陪葬,匈奴人甚至会用成百上千的人殉葬。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齐眉锯开,表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则镶嵌金片,当作酒杯使用。根据《汉书》的记载,证实匈奴人也有这样的习俗。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老上单于③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喝酒。事实上,匈奴人和斯基泰人都是猎头者④。希罗多德曾见过斯基泰人把砍下的敌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展示,还把敌
(本章未完,请翻页)
6匈奴的起源(4/5)
人的头皮挂在马缰上,四处炫耀。
公元6世纪的匈奴后裔,也就是***,有这样一个习俗,一个战士坟头上石头的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的。这种残忍的习俗也同样在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盛行。斯基泰人把敌人的血洒在插在地上小土堆里的圣物弯刀上,还要喝一杯取自第一个被他杀死的敌人的血。在订立盟约的时候,匈奴人会喝盛在人类头骨里的血液。在悼念死者的时候,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会用小刀割破他们的脸,“让鲜血混着眼泪一起流”。
匈奴人与斯基泰人一样,原本也是游牧民,他们生活节奏的调整与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息息相关。他们跟牧群一起迁徙,寻找着水源和牧场。他们只吃肉(这种饮食习惯给以素食为主的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穿皮革做的衣服,把皮毛当被盖,住在毡帐里。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不太明确的萨满教,这是一种基于对腾格里(T?ngri)或上天以及某些神山的崇拜的宗教。他们的单于或者首领,在秋季(牧马膘肥体壮的季节)召集全体匈奴人,以清点人员和牲畜的数量。在所有汉人著述者们的笔下,这些野蛮人都被描述成了抢掠惯犯,他们常常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农耕地区的边境,袭击人畜并抢劫财物,然后带着劫掠来的财物在任何反击到来之前迅速逃走。面对汉人军队的追击,他们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引诱汉人军队深入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或草原,在确保自身不会遭遇伏击的前提下,用雨点般的弓箭阻击追兵,却不贸然进击,直到对手筋疲力尽,因缺水缺粮
(本章未完,请翻页)
6匈奴的起源(5/5)
而失去斗志。这些方法之所以能够奏效,得益于他们灵活的骑兵和使用弓箭的高超技能。从最初的匈奴人,到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草原居民,他们都使用这些作战方法而很少改变。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还是西方的斯基泰人,只要是擅长骑射的部落都在使用这些作战方法。就像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斯基泰人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对付大流士。大流士及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且在“撤出俄罗斯”以悲剧告终之前就及时撤退了。然而后来又有多少汉人将领却缺乏这种谨慎,他们上了匈奴人的当,追击假装败退的敌人,进入了茫茫荒漠,最后却在那里被歼灭?
鉴于匈奴语在突厥-蒙古各民族中的地位,以白鸟库吉⑤为代表的一些作者倾向于把他们归为蒙古人种。伯希和的观点则与他们相反,经过对汉文译本进行几次交叉比对,他认为这些匈奴人总的来说应该属于***种,尤其是他们的政治统治阶层。
①见《汉书·匈奴传上》:“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②同上,原文是:“匈奴谓贤曰‘屠耆’, 故尝以太子为左屠耆王。”
③见《汉书·西域传上》,老上单于名稽鬻,匈奴冒顿单于的儿子,继冒顿之位成为匈奴单于,冒顿单于攻破了月氏,“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
④这里用的是它的本意,意思是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当作战利品。
⑤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蒙古民族起源》《东胡民族考》等。
(本章完)